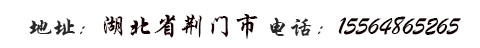贵州作家·微刊 桐月 小说《救火》
|
贵州作家·微刊 桐月 小说《救火》
第91期 贵州作家·微刊 作者小档案王安美,笔名桐月,女,年出生,贵州省福泉市人,汉族,本科文化。福泉市作家协会会员,黔南州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报刊杂志。 救火作者:桐月 “不好啦……不好啦……狗胜家的房子烧起来啦……狗胜家的房子烧起来啦!”朱大志一边往寨子里跑,一边大声喊叫。 此刻,寨子里正热闹,大家都在汤老五家院子里帮忙。汤老五的小儿子明天娶媳妇。寨上的人都来帮忙,大家正忙着收拾房前屋后、洗菜切肉、挑水砍柴。谁也没注意到,河对面狗胜家的房子着火了。 狗胜的大名叫陈启胜,是个外乡人,五年前,狗胜的家乡发大水,把庄稼全冲没了,为了生活,狗胜爸爸不得不拖家带口,来到打田冲投奔堂姐。我不知道狗胜的爸爸的本名叫是什么,只晓得寨上的人都叫他陈阿狗。陈阿狗老实、本份、勤快,寨上谁家有事,他都主动来帮忙,寨上的人都喜欢他。那年夏天,他们一家来到寨里,村民们把以前养猪的猪圈填平了,帮陈阿狗家修了三间土墙房,让他们有了个遮风避雨的家。 陈阿狗肯帮忙是出了名的,农忙的时候,谁家农活忙,他都去帮,到他家活儿忙的时候,寨上的人也都赶来帮忙,他家的农活总是一天就能干得差不多了。渐渐的,大家就把远一点的,自己不愿意去打理的荒山,送给陈阿狗,让他自己开垦出来种庄稼。地种得多了,陈阿狗一家也就不愁吃了。能吃饭肚子了,就该考虑娃娃读书的事,陈阿狗自己没文化,总不能让狗胜将来也没有文化,这样多没出息。 陈阿狗找到代诗军老师,决定把9岁的狗胜送到杨家沟小学读书。 狗胜以前不是叫狗胜,叫狗蛋。既然上学了,就该有个正儿八经的名字,进了学校,代老师问狗胜叫什么名字,狗胜笑呵呵的说:“老师,我叫狗蛋。”代老师笑了:“哪有叫这名字的,不行不行,这上了学就得有个像样的名字。” 陈阿狗摸摸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我和娃他妈都没读过书,也没正经给娃取过名字,大家也就这样一直叫了,都习惯了,也没想过啥正经名字,要不老师你给取个名字得了。”代老师想了想说:“这样吧,就叫陈启胜吧,希望孩子可以努力学习,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出人头地。” “要得……要得……嗯嗯,陈启胜好,陈启胜好,就叫陈启胜。”陈阿狗呵呵笑着。也就从此之后,大家都不叫陈启胜狗蛋了,但是,背着老师,却给陈启胜取了个绰号“狗胜”。 狗胜家是外来户,在本地还没有户口,就是大家说的黑户,所以狗胜在学校读书要交借读费,每个学期交30块钱。村支书杜友成见陈阿狗忠厚老实,就帮忙写户口迁入申请,寨上32户人家也都没什么意见,都签了字,盖了手印,就这样陈阿狗一家就把户口落在了杨家沟村打田冲组。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陈阿狗的老母亲去牛圈楼上抓草喂牛,从牛圈楼上摔下来,把脊椎骨摔断了。家里太穷,没钱给老母亲治病,只能这样瘫在家里,吃些赤脚医生开的草药,虽然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好歹命算是保住了。 早上临出门前,狗胜妈给婆婆擦了身子,服侍婆婆吃了饭,千叮咛万嘱咐要狗胜在家好好写作业,照看好奶奶,要给火盆里加够炭,不要把火弄熄了,奶奶年纪纪大了,不经冷。狗胜爽快的答应了。平时,狗胜就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狗胜妈也就放心地带着狗胜8岁的弟弟和6岁的妹妹出门,去汤老五家帮忙去了。 狗胜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炭火旁,把大表姐送给他已经磨得破了洞的帆布书包放在小木桌上,开始写作业。虽然那钉得不规整的门板上还蒙了一层麻布口袋,但冷风还是从四面八方灌进来。狗胜紧了紧身上的棉衣,把炭盆往奶奶床边更挪近了一点。这棉衣是村支书杜伯伯送来的,前几天,杜伯伯抱了一堆衣服过来,说是乡里救济的,杜伯伯可真是个好人呢,政府发的救济,他都亲自送到家里来。狗胜一家是打心眼里感激杜支书的。 写完作业,狗胜倒水给奶奶喝,换尿布,那娴熟的动作,一看就知道是经常照顾奶奶的,一点都不像个十一岁的孩子,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 “狗胜,狗胜,快出来,滚铁环去哦。” “你们玩吧,我不来了,我妈叫我在家照看奶奶。” “哎呀,来嘛,就在门口院子里转圈圈就行了,不跑远的,你时不时回来看一下就行了嘛,没得事的。” “那你们等等嘛,我给奶奶加点火,马上就来。”狗胜终究是个孩子,哪里抵得住一群小伙伴的劝说。狗胜把炭火往奶奶的床边更移近了一些,又怕火熄了奶奶被冷着,所以又往炭盆里加了些木炭,这才放心的出去玩。 刚开始的时候,狗胜还惦记着奶奶,玩一会儿就回屋里看看炭火,帮奶奶拉一下被子。玩了一会儿,一帮小伙伴觉得小院子施展不开,就商量着到马路上玩,狗胜想反正马路离家不远,自己又跑得快,几分钟就跑到家,去玩玩也不不打紧,一会儿就回来。再后来,玩疯了的狗胜直接把家里的奶奶忘到脑门后了。 狗胜在炭盆里加了足够多的木炭,这会儿,从那破板门里吹进来的风,让炭火愈发旺了。为了暖和,陈阿狗在老母亲的床棕垫的下面铺了厚厚的干稻草,那些从木床底下垂下来的稻草,在风中一摆一摆的轻轻晃动着。就这样晃啊晃的,就与炭盆里升起的火苗接上了,火在干枯的稻草上放肆的蔓延开来,稻草,棕垫,褥子,火越来越大。狗胜奶奶已经不能说话的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响声,声音很快就被大火吞噬。灰蒙蒙的天,掩盖了浓浓的烟雾,也掩盖了老人求救的希望。求生的意智使得不能动弹的狗胜奶奶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裹着被子从床上滚到了地上。 火越烧越大,狗胜家的房子,盖的是茅草,为了方便堆些粮食,中间用竹子编了一层阁楼,火把还没有干透的竹子烧得噼啪乱响,像过了期的爆竹那样沉闷。阁楼上堆满了几千斤木炭,那是陈阿狗给瘫痪在床的母亲取暖木炭,现在顺着烧断的竹阁楼,一点一点的垮下来。火苗窜上干茅草的房顶,借着风力呼呼的燃烧着,映红了灰蒙蒙的天。 一帮妇女在小河里一边洗菜,一边调侃,嘻笑声在打田冲的小山沟里回荡。邓幺妹和陈三娘把一筐洗好的大蒜苔抬到路边,回头一看,她吓呆了,对面狗胜家的房子火光冲天。“天啦,不得了啦,狗胜妈,快看啦,你家房子烧起来了。”随着她这一声大喊,小河里的嘻笑声嘎然而止,十几个妇女噌一下齐唰唰的站起来。 狗胜妈看着熊熊的大火,完全傻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半晌后,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娘还瘫在床上啊,狗胜还在屋里头,这该咋办呢,这杀千刀的狗胜,咋会把房子烧起来了,咋个办啊……”狗胜妈呼天喊地的哭,完全没了主意。“狗胜妈,你还在这里嚎哪门子丧,还不赶紧去救火。”赵三娘一边拿起洗菜盆往狗胜家跑,一边吼狗胜妈。被她这么一吵,大家才反应过来,七手八脚提起菜盆,水桶,跟着赵三娘跑。 半路上,赵三娘和赶来报信的朱大志撞了个满怀。“火……火……狗胜家……”朱大志上气不接下气的说。赵三娘打断朱大志:“大志,你跑得快,快到山上去把砍柴大人们找回来救火……快去……” 赵三娘带着一群妇女,慌乱的从屋前槐树下的老井里取水灭火。火势太太大了,一盆盆的水浇过去,却起不到一点点作用。茅草盖的屋顶顺着烧断的房梁不断的垮塌进房子里。“轰!”又一根房梁垮塌下来。 “嘭”的一声,空气里瞬间飘出一股肉烧起来的酸臭味道。“哎呀!陈大娘的肚子烧爆了”邓幺妹没头没脑的喊了一句,大家这都呆住了。瞬间,嚎哭声响成一片。 男人们赶到的时候,房梁,茅草屋顶全都烧得垮塌进屋墙里了,光秃秃的土墙里火苗带着黑烟高高的窜起,土墙里面不时传来木炭燃烧的啪啪声。 狗胜站在院坝里,已经吓得尿湿了裤子,两只手死死的扯着衣角,下嘴唇已经被他咬出了血。陈阿狗一把揪过瑟瑟发抖的狗胜,一脚踢摔倒在地上:“你这个背时娃儿,老子千辛万苦把你们拖到这个地方,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才算有个家,我娘苦了一辈子,还没享过一天福,就被你这不孝子孙一把火烧得骨头都找不到,老子今天非要打死你这个孽子不可。” 陈阿狗那一脚踢得着实狠,狗胜趴在地上楞是半天没爬起来,不知道是踢坏了,还是吓傻了,连哭都没有哭。陈阿狗提着一根二指宽的木条,劈头盖脸的往狗胜身上一顿狠抽,大家伙赶紧过来拉。 杜支书和几个小伙子刚好赶来,手里提着抽水泵,看到陈阿狗打狗胜,气不打一处来:“陈阿狗啊陈阿狗,你不救火,在这里打娃娃,我看你是疯了,你们放开他,让他打,几千里路来到这个地方,不就是为了娃娃么?事情都发生了,你就算把他打死,又能弥补哪样?我看你那脑壳是横起长的,别的没学到,打人的本事倒是不小。” 见陈阿狗呆站着,又吼道:“还不快点把抽水泵放到井里去,我怕再烧下去,你是真的连陈阿奶的骨头都捡不到一根了。” 被杜支书一骂,陈阿狗这才回过神来,赶忙去井里抽水。村民们一部分负责用水泵抽水,一部分用盆端,一些用桶提……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下,总算是把火烧灭了。 杜支书带着大家伙儿在腾腾冒着热气的木炭里小心的翻找着,还不时叮嘱:“轻一点啊,老人指不定烧成什么样了,一定要轻一点,要保证遗体完整啊!” “唉,可怜陈大娘一天好日子都没过到啊,造孽啊!” “杜支书,找到了找到了,这里好像有只手,你快过来看看。”一个人在火炕边发现在陈大娘的尸体。 杜支书带着大伙,小心翼翼的翻拔着木炭,不一会儿,烧得漆黑的尸体被刨了出来,一只手已经烧没了,另一只手死死的抠着火坑边上的石头,不难想到她死前用尽力气无助的苦苦挣扎。陈阿狗一边哭一边去掰扯那只手,被大火烧脆了的手指经不起外力,两个指头硬生生掰断了。 杜支书叫人找来两块板子,把尸体用麻布小心翼翼的裹好,放在木板上。这时候救火的人围拢过来,陈阿狗“扑通”一声跪在了板子旁边,双手搭在裹着麻布的尸体上不停地念叨:“娘啊!是儿子害了你啊,是儿子害了你啊,儿子不孝啊……”那悲惨的哭喊声,久久回荡在人群里。杜支书慢慢走到陈阿狗身边,望着他那满是鼻涕眼泪的脸,蹲下身子,双手搭在阿狗的肩上说道:“阿狗啊,人死了就活不回来了,你要挺住啊,你还有婆娘,还有三个娃娃在指望着你呢!你倒下了,你让他们怎么办?你在这里陪陪老母亲,接下来的事情还有党和政府,还有全村的父老乡亲,现在关键的是先想办法把陈阿奶的后事安排了。”右手轻轻地拍了拍陈阿狗的头。 大家习惯性地围拢到了杜支书的身边。杜支书环望了大家一圈,眼眶里的泪水快要淌出来了,眨巴着眼,抬头望了一会天,低过头来说:“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有句俗语说——老人在生的时候是自己的老人,死的时候是全寨子里的老人。阿狗子来到我们村已经有些年了,他平时在村上也是东家忙西家跑的可没少尽力,是个老好人啊,现在他家摊上这档子事,父老乡亲可不能看着不管,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吧。” “我们不会办事,你是寨子里最有主意的人,又是村里的支书,你安排,我们一定全力办得妥妥的。”组长杨志成抢话说道。 “杜叔你就吩咐吧,我们听你的,听你的……”“是啊,是啊……” “好吧,现而今出了这档子事,白喜和红喜同时撞上了,这在我们村还是第一次撞上,大家都得费点心思了,得把两边都兼顾好,都要要办妥当了。”杜支书说完这翻话,又转过身来对杨志成一眼说:“志成啊,当务之急是你先去叫几个后生,到后山去砍两捆竹子来,先给陈阿奶搭个简易灵堂,还有,去把主持丧事的杜公公请来一起料理阿奶的后事。人死饭蒸开,现在陈阿狗是什么都烧没有了,你去跟管村账务的牛会计一起合计看看,该采买什么就去买,先用村里集体资金垫付一下。”顿了一下接着说“你这边就先这样子,落实去吧。” “哎,哎”杨组长连哎两声就吆喝人去了。 杜支书转过身来,对赵三娘说:“他三娘啊,你是妇女主任,接亲办酒这码事你也熟络,汤老五家那边就交给你承头了。新娘家来人要款待周到,不能冷落了亲戚。还有啊,狗蛋三姊妹还小,也守不了夜,他们爸妈这几晚可能管不到他们了,你也顺带安排几兄妹的睡觉的事吧。”“哎!哎!他杜大伯,这些小事你就放心吧,交给三娘我保证办的妥妥的。”赵三娘吆喝着一帮娘子军赶往汤老五家去了。 天更阴沉了,山风呼呼地刮着,带着一丝刺骨的寒意。杜支书转过身来,陈阿狗仍然跪在陈阿奶的遗体旁,耷拉着双肩,嘴里还在念叨着:自己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让老母亲过上一天安稳日子,临了更是让老母亲不得好终,真是作孽啊……平时看来那么有分寸的人,怎么到关键时刻没有主见了?也许,我们不是陈阿狗,不能体会陈阿狗的痛吧。 杜支书的目光从阿狗身上移了过来,又落在裹着麻布的陈阿奶的遗体上。杜支书布满岁月沧桑上的脸上神色很凝重,山风吹来,不觉打了一个冷噤。是啊,陈阿奶往日在寨子里家里家外忙碌的身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浮了上来,劳碌一生,穷苦一生,最后落了这样的结局,老天不公啊! 在杨家沟村最讲究人活着不管怎样穷苦,死了,要有个好归宿,要有一口好棺材,现在,老天眼瞎,一把火把陈阿狗刚刚建立起来的家都化为灰烬了,阿奶的归宿在哪里呢……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先把去年自己为老母亲杜奶奶准备的那口棺材拿来用了。想到这,老杜的头脑里这样一闪:记得去年前的春天,在家里闲不住的杜奶奶,拖着80高龄的老身躯去后山竹林里打笋子,一不小心滑了一跤从地坎上摔了下来,大腿根被往年砍下的竹根儿戳穿了个洞,幸好当时也在坡上打笋子的狗胜妈见着了,跑来山下喊人去抬了过来。抬到家时老人几近昏迷,人老了,加上受凉,又摔得不轻,老人在床上服了整整一个月的草药,才算挺了过来。那期间,杜支书生怕老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赶紧卖了家里那头陪自己过了12个年头的老水牯牛,置换了今天搁在神龛背后的那口老棺木,以备不时之需。现在陈阿奶的这种情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顿了一下,老杜抬起右臂朝人群里挥了一下:“杨二叔、杨三叔、杜二狗子、小沈……你们几个跟我来一下。”大家围拢过来。 “你们几个都过来去我家抬口寿木来,给陈阿奶用上。” “去你家?不会是去搬给我杜大奶奶置备的那口寿木?”杜二狗子咕叨道。 “是的,死者为大,先给陈阿奶安上个家,之后你杜大奶的再想办法吧。”杜支书平静地回道。 天渐渐黑了下来,山风仍在呼呼呼地鸣响,风声里夹杂着山村的深冬里特有的稀落落的冷雨。冷雨不时飘进嘴里,那种咸咸的带着炊烟的味道,只有山里人才能分辨出来。没有月亮,汤老五家那边稀疏的灯火散落在天幕上,衬出远山朦胧的轮廓。村民们在阿狗被烧塌的房屋废墟和那并不开阔的院坝上忙碌着,拉电线接灯的、从寨子头搬板凳锅灶的、劈柴烧火做饭的、清理老屋废墟扯竹竿搭灵台的…… 人们安静而有序地各自做着事,很少有人说话。东村那老巫师被请来了,她头上罩着一块黑布纱,双手捧着一碗米,碗里插着三炷香,口中念念有词,不时又伴着一声凄厉的长哨,朝放着陈奶遗体的木板处走来。老巫师把碗放下,抽出香来向陈奶的头部画了个圆圈,同时大叫一声:“咿呀嗬!小鬼精精快滚开,如来佛我从西边来……”接着又围着陈奶的尸体唱唱跳跳跑了三圈,最后才在尸体前坐下来念唱,给亡魂招魂。 天已经黑尽,冷雨凄风渐渐加剧。挂在四周的电灯照亮了灰蒙蒙的夜空,从各处拢来奔丧的乡亲也多了起来,杨组长带人从镇上买来了丧葬用的物品。先拿出几个大炮竹来点上,砰!砰!砰!三声响彻天空的炮响,那是代表逝者安然落气的鸣吼,砰!砰!砰!又是三声脆响,那是代表逝者将要敲开天堂的大门。炮响过后,杜支书组织大汉们也把棺木抬到了,他们先是把棺材放在两根长条凳上,解开捆住棺材的绳索。 棺盖揭开,杜八公公拿来大把草纸铺在棺材内堂里,认认真真地铺了七层。然后让陈阿狗来到棺材前面的火盆前,跪在地上往火盆里烧七斤九两纸钱,把灰用白布袋装好,给陈奶奶做枕头用。然后就是给逝者剃头洗澡换寿衣。当地的习俗,过世的人要用香枝树的水把身子洗干净,来世才能投个好人家。陈阿奶的头发已经烧成焦炭,只简单清理一下就给换衣服了,换衣服可是一件难事,其场面也惨不忍睹,虽然已经很小心了,但是还是把一只脚弄脱断下来,杜八公公小心地把弄脱断的脚和早先掰扯掉的两个手指头安放在遗体上…… 按习俗,换好衣服后,还要化妆再入殓的,陈阿奶被烧焦的尸体根本没办法化妆了,杜八公公没办法,只能直接和旁边的几个阿公一起把陈阿奶的遗体搬离木板,直接抬进棺材里去了。再用纸钱填充陈阿奶和棺材的空隙处,直到填满填实,最后用一贴纸钱搁在陈奶的额头处,还在她的手上夹了16.6元人民币,据说富有人家可以夹.6元,6元不等崭新的人民币。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八公公示意陈阿狗过来棺材前面:“阿狗啊,按规矩办,你现在喊妈三声吧,让老人家安心的去吧。” “妈!妈!妈!”陈阿狗嘶哑的连喊三声后,就被人拉开了,两个年轻人把棺材盖上,并用两片新翻开的竹条紧紧地捆在棺材的中间。 遗体盖棺,守夜算是开始了,村民们三三两两的围在一堆堆燃烧起来的炭火旁。不时谈论着一些人死不能复生、在世要好好活着、人生过得真快等等。半夜十二点,大家也都饿了,杨组长组织开宵夜了,根据人数,摆了6桌的烂肉饭,就是丧饭,村民们边吃边喝边聊,算是陪死者渡过在阳间的最后一夜。 第二天,大家在家休整一天,晚上孝子和一些亲朋依然要守夜。第三天清晨5点40分出殡。主持丧事的杜八公公唱了声:“咦哟嗬,起。”八个人同时把棺材抬了起来,此刻,炮竹声、唢呐声、鼓跋声、孝女的哀嚎声同时开演,一时间响声大作,传遍山野。在棺材肚子下牵出一根长长的大绳来,送葬的人就牵起大绳走在棺材的前面,阿狗穿麻戴孝端着遗像走在大绳的前面,遇上爬坎过沟时,棺材就会停下来歇气,陈阿狗就会转过身,跪在送葬的队伍前面磕头。唢呐、炮竹,又同时响起,等唢呐一停,鼓和跋又接着响起来,妇女的哭唱声也跟着提升,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开,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久久回荡。 棺材抬到了坟场,井早已挖好了。杜八公公把系在棺材上的母鸡一把抓下,在喉咙处宰了一刀,倒提着,把鸡血淋洒到井底。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孝子跪在井边,头伏在地上,对帮忙的相亲表示叩谢。阴阳先生摆弄着罗盘,不停地调试着最佳的脉象,杜支书拿起抬棺材用的横梁,不断地跟着罗盘的方向拨弄着棺材的方位。脉象找好了,杜八公公清了清嗓子喊道:“孝子盖第一铲土。”陈阿狗盖完第一铲土后,身旁的乡亲才围拢过来七手八脚地一起盖土、挖草饼、砌坟身。 中午,从坟场上帮忙的乡亲陆陆续续地回来吃中午饭了。陈阿奶的后事算是告一段落,尽管仓促、简单,但老人也总算入土为安了。杜支书还没有去坐桌子吃饭,他还伫立在陈阿狗家被烧掉的房屋废墟前,久久地盯着已经燃烧殆尽的立柱木、房梁木,还有那些烧得发黑的光秃秃的土墙,不时皱皱那紧锁的眉头。这时候,小组长杨志成和陈阿狗一起过来招呼老杜去吃饭。杜支书慢慢转过身来,望着他两说:“陈阿奶已经入土为安了,可是活着的人还没有安身之处啊!”说完长吁了一口气。 陈阿狗连忙回答道:“杜支书啊,狗蛋奶奶的后事已经让你费尽心思了,还有你杜奶的棺材这事,更让我过意不去,等忙完这事,我和狗蛋妈妈得出去打点零工,尽快把杜奶的棺材钱凑齐才成啊。我娘的后事,我们一家已经对你、对乡亲们感激不尽了,至于以后我们一家大小的安身之处,我已经想好了。” “想好了?去哪里住?”杜支书有点疑惑了。 “我们一家就去后山的那个山洞住吧,洞里冬暖夏凉,蛮好的。”陈阿狗说完这番话,也长长的吁了一口气。 “这哪能去山洞了里住啊,现在已经不是白毛女的时代了。”杜支书果断地拒绝了陈阿狗投来的期待的眼神。接着对杨志成说:“杨组长,趁大伙还在吃饭没散去,你去各饭桌上交代一下,让大家吃饭好以后去村委会门口集中,集体商讨一下陈阿狗家的事。” 说完,一手拉着杨志成,一手拉着陈阿狗:“吃饭去!” 天空的乌云已经悄悄地散开,冬日里那久违了的阳光也露出了温暖的脸。 杨家沟的村委会就设在打田冲组的村头,村头道路两边耸立着两棵高大苍老的大榕树,两棵榕树的树根下面摆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被磨得光滑程亮的鹅卵石。村委会办公室就在两棵大榕树的正对面约50米远的地方,村委会办公室是一座两间的两层小平房,门口立着一根高高的木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迎着风儿高高地飘扬着。在平房和榕树之间的空院坝,就是平日里打田冲山民们议事和休闲娱乐的地方。此时,打田冲的山民们已经齐齐的赶来了,三十来户人家,除开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老老少少大概也就百十来号人。陈阿狗一家也站在了人群里。村委会办公室里,杜支书、杨组长、牛会计、杜八公公等七八个人,正围着一张大圆桌在谈论着什么。杜支书的位置正对着窗口,他从窗户上看到院坝上人头攒动,左顾右盼,于是放下手中的笔,对着在座的人说:“唉,大伙已经来得差不多了,出去招呼大家吧,剩下的事晚上再来。”说完就先起身朝门外走了出来。大伙也跟着走了出来。 杜支书一边冲人们喊,一边快步蹬上了门前小旗杆台上。每当站在五星红旗旗台上讲话,杜支书就感觉特别的精神,也特别的踏实。他习惯性地冲大伙点着头,扫了台下的人群一遍后,正着身子,双手扯了一下衣角,顿了顿,亮着嗓门说:“乡亲们、老少爷们,你们辛苦了!今天,临时召集大家来这里的目的,相信大家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现在我就长话短说吧。狗蛋家,因为一时疏忽,被一把火烧了,烧得什么都没有了,正所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把火烧回到解放前啊!每家都难免会摊上点小灾小难,所以今后我们大家一定特别要注意防火防水、防电等安全啊!现在,狗蛋爹说,要把家安到后山的山洞里去住,山洞里阴暗、潮湿、蚊虫多、蛇也多,大家同不同意他们家去山洞里住啊?!” 这下,人群里像炸开了锅一样,“不同意、不同意”的呼声此起彼伏……也有的人在议论:家都烧得片瓦不存了,不去山洞里住又去哪里住呢?他们家刚刚辛辛苦苦搞了三年才搞好的房子,还没住多久就被大火给烧掉了,现在又去哪里找钱来搞新的呢!真是作孽啊!可怜啊!说着,说着,有几个老奶奶经不住留下了热泪,赶忙扯衣角擦拭。平时跟陈阿奶最要好的杜八奶奶更是失声痛哭了起来。越哭越是伤心。整个会场经几个老人家一渲染,气氛变得伤感、紧张了起来,全场一片哀声叹气,一副副愁苦悲哀的神情,弥漫在打田冲山民们的眉宇之间。 “我们大家一起来帮狗蛋家修建房子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帮狗蛋家修建房子吧!”声音显得特别的大,是从大嗓门赵三娘那里传来的。三娘连续的呼声点燃了人们的情绪,人群里不时传来:“是啊,是啊”“好啊,好啊……”“我们人多力量大,一家出一点力,帮衬一点就能帮狗蛋家重建新房,渡过这个冬天了”……渐渐地议论的声音越来越来小了。 村民们似乎约定好似的,齐刷刷把目光投向了还站在旗台上的杜支书身上。杜支书脸上浮现了难得一见的会心的微笑,感觉是时候了,连忙双手举过眉宇示意大家静了下来。提高嗓门,大声说道:“大家伙的心声,我也看到了,听到了,这也是我们打田冲组全体成员的优良传统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几天我们暂时放下自家活路,先用几天时间帮忙一下,捐款、捐物、出力,突击把阿狗的房子先立起来!刚才我们村委几个成员初步商量了一下,决定成立一个建房临时筹备小组,杨志成任组长,负责统筹安排各项建房工作,牛会计负责登记好捐来的钱物,做好物资预算,伙食安排等,我嘛,就负责想办法去找社会力量援助,找党和政府申请住房资金补助等。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协作,一定会给狗蛋家重新修建出一个温暖的新家的!” 杜支书的话语是多么的响亮、有力。刚说完,会场上就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息,回荡在打田冲小小村庄的上空。 杜支书又伸出双手示意大家停下来:“现在,大家伙就可以先去帮狗蛋家清理老屋基的废墟了,等明天方案出来了,再按方案去办。对了,陈阿狗,你们一家就先在我家老屋挤挤,老屋虽然破旧了,好歹还能避着风雨。”说完刚想离开旗台,突然看见陈阿狗一家手拉着手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杜支书啊,我有话想说说啊!” 陈阿狗热泪盈眶,一手拉着狗胜,一手拉着狗胜妈站在中间,狗胜拉着弟弟,妈妈拉着妹妹站在两边。待一家人站好后,陈阿狗带着一家人对着台下大声说:“我们全家谢谢乡亲们了,谢谢乡亲们了。”第二个谢字刚说出一家人已泣不成声,深深地鞠了一躬,又转过身朝着老杜也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们全家也谢谢杜伯伯、谢谢杜伯伯了!”“哎呀,就不要那么客气了嘛!乡里乡亲的,说这些搞哪样啊。”赵三娘边说边从台下跑了上来,“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有难,哪有不帮的理儿啊,走吧、走吧,回去吧。”三娘一把扶起狗胜娘和孩子,与杜支书一并把他们拉了下来。乡民们见状也各自慢慢散去了。 小山村的深夜万籁寂静,没有月亮,从远远的地方就能望见村委会那栋小平房的灯还在亮着,有几个人影不时在晃动。大伙快要离开的时候,杜支书又交代了一句:“明天你们就按既定方案去安排人手砍伐树木、竹竿,搬运石块,砖头、瓦片,还要注意做好群众思想动员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都能有序开展。好吧,你们先走吧,我再花几分钟时间打份报告给乡里,刚才乡政府的郭书记还亲自来电话问起了陈阿狗家的事儿呢,说是给陈阿狗家是特困户,乡里特别拔下了块钱的救助款,我打个证明让陈阿狗去领救助款!” 在政府和关怀和扶助和村民们的齐心协力帮助下,一个星期之后,在狗胜家原来的屋基上,又重新立起了三大间崭新的红砖瓦房。 冬日暖暖的阳光装满了整个堂屋,照在陈阿奶慈祥的遗照上,屋檐下,两只喜鹊也正在忙着衔来新鲜的泥土赶趟儿地在垒筑他们的新家呢。 贵州作家·微刊编辑指导委员会主任:欧阳黔森副主任:孔海蓉李寂荡何文杨打铁王华赵朝龙戴冰禄琴唐亚平赵剑平黄健勇韦文扬苏丹喻健姚辉主编:魏荣钊执行主编:杨振峰贵州作家·微刊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北京专业的白癜风医院北京专门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guizhoushengzx.com/gzsjy/1358.html
- 上一篇文章: 贵州举办“丝绸之路·黔茶飘香”推介活动
- 下一篇文章: 贵州兴义齐鑫胡蜂养殖技术开始培训了